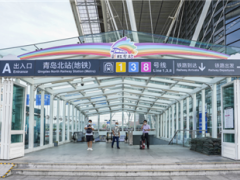【范正安简历】1945年出生;1957-1965年泰安曲艺团演员;1965-1971年广州军区战士;1971-1994年泰安市食品公司司机;1994年退休;2007年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山皮影传承人。
范先生您好!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《泰山旅游发展四十年口述史》课题组的采访,您是泰安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代表,您携泰山皮影一路走来,所走过的路也印证了我们国家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发展历程,能简要谈谈您的经历吗?就从从师学徒开始,谢谢。
范正安:感谢你们的采访,这是给我的机会。非常欢迎王校长带领亓老师来到我家进行采访,我得首先感谢校长对我长期的关心、支持和帮助,这年来一直为我和泰山皮影鼓与呼,我很感动。
我小的时候,咱泰安不叫“皮影”,叫“挑影子”,这个有来历。当时因为老艺人没有什么交通工具,就是一根扁担,都是挑着担子,往肩上一放就走。前头挑的是戏箱,里面装着的都是皮影、幕布这一套,后面挑的是被子褥子这一套。时间长了,老百姓一看见他们挑着担子来了,就说挑影子的来了,“挑影子”这个名就叫响了。后来,又深入了一步,因为泰山的皮影演出操作的时候,要用一个杆,用杆来挑着用驴皮做的皮影上下左右的动,泰安人就又把皮影叫“挑(tiǎo)影子”。这样从挑担子的“挑”(tiāo),到上挑的“挑”(tiǎo),字是一个字,声调不一样,意思也不同了,但写成字的话,都是“挑影子”。现在年轻人不一定知道了,到六十岁以上的老泰城人一般都知道。
我算记事比较早的,四五岁就开始记事了,我当时就经常听俺大大还有叔叔大爷们说,咱泰山有个挑影子的挺好。从四五岁的时候,我脑子里就灌满了挑影子,还经常听到老人们模仿着唱两句,在心里好像就扎根了,就想看看,这个挑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但一直没有机会看。记得六七岁时,泰城的古城墙所在地,也就是现在的青年路,那里有个西门,西门的里面有一块儿空地,就算小广场吧,经常有挑影子的。那是谁呢?从我现在的辈分来看,那是我的师爷、老师爷,他们在那里演。想看,但挤不进去,不敢说是人山人海吧,但每次都是一大堆人在那里围着看,我们这些小孩子根本挤不进去。去过几次,看不到,光听着大人哈哈地笑,弄得心里挺痒痒的。真正第一次看到,是我八岁那年。那年我的小伙伴告诉我,说在南河森那里来了挑影子的了。只有老人知道南河森这个地方,就在渿河十二连桥北边那个一片,对着现在河东卖五金的这一片的西侧。南河森这个地方的环境太好了,到今天我还很怀念。渿河水从山上流下来,有沙滩,还有几百颗大杨树,清清的河水,高大的杨树,雪白的沙滩,那环境是真好啊。
为什么选择到南河森这里来呢?是因为要保护岱庙。解放前,说书的、唱戏的娱乐场所都集中到岱庙里了,解放后,党和政府很重视古迹文物保护,娱乐场所在岱庙可不行,破坏了古迹文物那还了得,就把这些娱乐场所放到南河森了。在树林当中有五座说书的棚子,每个棚子有200来平方米吧。内外都很简陋,平平沙滩,埋上柱子,用高粱秫秸秆编的箔一围,用黄草做顶子蒙上;里边的凳子更简单,是把两个橛子打到沙滩里,再把一块平板钉到上面,一排排的,十来排,前面还有一个说书的台子。变戏法的、卖大力丸的、算卦的、赁小人书的,都上这里来了,但以说书的为主,主要是曲艺类的。有一间比较大的是挑影子的,白天不演,只是晚上演,我早知道了,但不敢来,人家不白演,现在叫买票,那时叫买牌,是个小竹子牌,一个牌是二分钱。能看一个多小时,咱没钱啊,也不敢去。到八岁这一年,小伙伴一说,我敢去了,为什么,咱有钱了,总共加起来有两块来钱,就觉得心里柱壮了。钱怎来的呢?靠那时的孩子勤劳啊。我的家庭比人家还艰难一些,因为我五岁那年父亲就病故了,家里刚剩下俺娘和几个孩子。刚刚建国,都穷啊。就想着怎么减轻当娘的负担,孩子吃不上,当娘的更吃不上,她想法讨弄一点来就先给孩子吃。看着俺娘整天劳顿操心为难,就想干点什么,挣点钱,用现在的话就是减轻老人的负担。就模仿着人家干点活,一种方式是上山去刨药材去,刨黄芩、香附。香附哪里多呢,从南河森向南,到南湖那边,当时那个名挺吓人的,叫“黑咕咚”,现在知道这个名的不多了,渿河到了那里是个急拐弯,平常很少有人去,再早以前刑场大部分设在那里。那里有很多香附,一片片的,我就背着小筐子,拿着小橛子,去刨药材,这是一种方法。再一个呢,是满大街捡人家扔的橘子皮,回来洗干净,晒干了,拿到药店去卖,陈皮是一味药材啊。还有就是,养牛养马的需要草料,我就割草去卖,弄一大挑子,也就给个三分二分的。有一次卖陈皮,还有黄芩,一下子卖了一块多,心里挺恣儿。就用这种法攒了两块来钱。这两块多钱,我给俺娘一块二,自己留下了几毛钱。这回有钱了,就跟着小伙伴去看挑影子,结果还被俺那小伙伴砸了一杠子:一块儿跟着去了五六个人,我就咬着牙说我请客了,都到跟前了,不请也不行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看皮影,当我看到皮影时,用现在的话说,那叫一个震撼啊!那时俺师傅演的是东游记,是下八仙里的金眼毛遂,从地里钻出来,抱着朱顶大仙的腿,拿着小刀就攮。哎吆,我一看,能上天、能入地、能驾云,那里见过这个!这第一次就把我吸引住了。从那之后可就麻烦了,脑子里时时刻刻就在想,就想看,就想学那个东西。现在想想,我这人可能就是为这个事生的,你看看,从那时到现在从没离开过皮影。
八岁看了皮影以后,就再也割舍不下了。我上过几年小学,是九岁上的。老是放不下皮影,每天想方设法得看皮影,那时学校也没那么多作业。放了学,家也不回,饭也不吃,就到演皮影的棚子门口等着去。说真的,腰里那几毛钱不搁花啊,没几天就没了,没了还想看,怎么办呢?为了看皮影我逃过学。有一段时间,一大清早我背着书包走了,俺娘以为我去上学了。老师到家里问,家里有事吗,孩子怎么七八天没上学了,一下就露馅了。俺娘让俺哥把我揍了一顿,为什么白天没去上学呢?那时因为看皮影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个事:白天,俺师傅在树林里的大树底下放张桌子,闷上壶茶,在那里刻皮影。我一看这是学习的机会,连学也不上了,就去看,那时候人家不认得我,不让围边,就老远地看,看怎么弄、怎么画,就是看步骤啊。一看七八天,就挨上家里揍了。现在看揍得对啊,你不好好上学去干别的不应该啊,但我就是放不下。
后来,光看师傅演、听师傅唱就不满足了,我就拿着铅笔画他的造型,用现在的话就是速写。后来有人问,你小小的孩子就有那个水平吗?水平说不上,但确实是有心,人在某方面可能多少有点天赋,尤其是自己又是喜欢这个。当时没有钱买纸笔,就到西边大堰北的南边有个山,是滑石山,挖点滑石当笔。那时我住在元宝街,街道全是两米长半米来宽的石头条子,就在那上面用滑石画。有好多次我画的画大人都停下来看看,说这孩子画得不孬。为了提高水平,我到庙里临摹壁画,在家门口的万圣宫,还有灵应宫,都有不少壁画。后来多少有个钱,就买个本子和笔来画。我说这个是表达一个意思,就是人们说的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”,我走到今天这一步,就是兴趣引导的。白天逃学去看师傅刻皮影,就认为比上学还重要。白天看还不行,晚上还想看演出。钱没了怎么进呢?就想办法,后来概括起来就是几个办法,第一是钻板凳,第二是挖窟窿,第三是当孩子。钻板凳就是利用他演出的间隙,观众往外走,我往里钻,钻到板凳底下,当时光线不大好,人家监场的一看没人了,就把下一场的观众放进来。我就混到里面看一场,这个办法长不了,慢慢人家监场的就知道了,人家高兴就装看不见,不高兴就提溜着耳朵给拽出去,大冬天家把耳朵都拽得通红。这个法不行了,有一次连续四五天捞不着看,急得团团转,把耳朵贴在秫秸上,光听也不过瘾啊,就想进去。后来想了法,我把泥巴秫秸墙的泥巴抠下去,用小刀把秫秸抠一个洞,钻进去看,这个办法只用了一次,第二次,刚把头伸过去,里面两只大手就把我的头给薅住了,说你小子把好好的秫秸给弄了个大洞,一脚就把我踹出去了,头上弄了个大包。我说这个就是想说明我当时真是对皮影着迷了。又想了个法,让大人带进去。见了慈眉善目的就叫爷爷,年轻点的叫大爷,就说,我想看挑影子,能把我带进去吗?遇到好心的就带进去了,也有不理你的。我就想,有什么长法,来了就能进。后来想了个法,还真管了大用了,是一散场了帮助人家打扫卫生,观众吃的瓜子、抽的烟头、吃的糖纸满地都是。开始,我从家里拿着笤帚,站在剧场门口,我不进,等一散场,我进去就扫地,人家管剧场的包括俺老师就喊,哪来的孩子,俺不用你,走吧走吧。说也不管用,我笑嘻嘻的,干得特别带劲,扫完就找个簸箕撮出去。开始他们还撵我,后来不撵了。这样扫了四五天,我再去,人家把门的就说,扫地的来了,进去吧。吆嗨,成了!从那以后就畅通无阻了。我一想还不行,还得进一步,再提高提高。又发现了一个问题,那时人们喝水都没有暖瓶,买不起啊。偶尔看到师傅演出时,端起杯子喝水,结果杯子里没水,我看到机会了。再演出时就给看门的人要个牌,一个牌能在卖水的地方打一壶水。我就提着壶到幕布后面给师傅去倒水,一掀开帘子进去了,师傅就停了一下,因为一般人不让进去。看到是我给他倒水,就笑了一下,我一看有门,这样就给师傅拉近感情了。以后我一到剧场,先给师傅倒水,水凉了就换水。后来,不但我自己进去,还能带着小伙伴进去。小伙伴知道我能进去,就打招呼让我领进去,我说行,你得打扫卫生。通过这个,我悟出一个道理,你要想获得,必须得付出。同时,要尊重老人,尊重老师。就因为我有了这个便利条件,我在做皮影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。我在粮食市小学上学,当时都有美术展览,每次我做的皮影都拿出来展览,什么题材的都有。有老的传统题材的,也有打日本鬼子的,还有现代的题材。万事一理,你要学东西,不用心不行,干么有么的道理,得找清里边的道理、方法。这一切,对我来讲,归结到两个字,就是因为“喜欢”。
这样就和师傅一块儿弄了好几年,到了1957年,有了个机会,当时听到消息,政府要组织艺术高、德行好的老艺人成立曲艺团。曲艺团里面有相声、山东快书、山东琴书、渔鼓,还有评书、皮影。后来我了解到山东成立曲艺团,有两个地方有皮影的,一个是泰安,另一个是德州。济南有皮影,但没进曲艺团。皮影进入了曲艺团。那时候可能就考虑到传承的问题了,皮影给了三个名额,我一听高兴了,赶紧找师傅,我叫刘老师,您看我能行吗?那时还不敢叫“师傅”,师傅说,我听说你做皮影刻人物还行,拿来我看看。我一溜小跑到家了。因为那时我做皮影包括演皮影在元宝街、大观街、灵芝街一带已经有名了。学着做皮影,就想演皮影,怎么演啊?我在我元宝街的门口,门口那边还是比较宽的,我要想演,晚上就搬出吃饭的桌子,绑上两根杆子,把俺娘用的包袱当幕布,弄个灯,我就演,好几个街的人来看。演了几次,耗不起油,俺娘就不干了,这些油还得吃啊,都叫你点了灯怎么能行?我有法,就先搭台子,有来看的小孩,我就问,你想看吗?想看,好,想看就回家拿点油去。一酒盅子就行,这个拿那个拿,人一多有时还用不了,能拿回去吃。看有些家庭条件好的,就动员他回家拿蜡烛来,都疼孩子啊,就给钱买蜡烛来,挺红火。这个事,俺师傅已经有所耳闻了,我回家把最好的皮影拿给师傅,师傅说挺好,夸了我。又问会唱吗?会唱。但心里紧张,又想到这个时候了,就唱吧,我就拿着筷子敲鼓点,乐器怎么个打法、影子怎么个挑法,这一切我都从师傅那里全仔细观察好了。我唱的是《杨二郎》,俺师傅一听就说,你这个徒弟我收了。当时一听真高兴。师傅又问家里的老人同意吗?我还真没问来,师傅说,家里不同意我们不能收,这是规矩。我心里说,这个问题不大啊。回到家,家里人都回来了,我姊妹五个,俩哥俩姐,我最小。吃饭的时候,俺娘说我想学皮影,问大家同意吗。俺哥立马就说不行,说那是要饭的活,不能学那个。俺父亲去世了,家里就靠俺哥。那时说书的、说相声的、演皮影的,地位很低,人分三教九流,这些人是下九流啊。封建社会,这些艺人的后代想进仕途都不行,没资格啊。就是现在,人们思想上恐怕也多少有些残余啊。俺娘就马上说,不能学那个。我说我非学不行,俺娘说,你学就揍你。为了抗议,我不上学了。这样三四天以后,老师就找到家里来了,是小学宋汉臣老师,宋老师说,无论如何你得学好文化,干什么也得有文化,一点也没错。但我听不进去,其实那是我有两个理由,一个是喜欢学皮影,一个是听说进曲艺团有工资,把工资给俺娘多好啊。当时我上学交不起学费,得上村里写免费证明,俺娘为了给我写证明去村找村干部,去个十趟八趟地都写不回来,人家都不理你,一看真够了。咱虽然小,但也要尊严啊,咱自己不要紧,俺娘得在那里等着,人家不耐烦地说,没空,以后再来吧,这样一想,也不想上了。老师来家里三次,我就说不去上学了。最后俺娘和俺哥就问,真想去学皮影吗,我很坚定地说:想学。那好,你自己看着办吧,松口了。我直接去给师傅说,家里同意了。光你说不行,我得问问去。一问俺娘,俺娘说本来不愿意,但孩子拗,就叫他学去吧。师傅说,好了,你到棚里去就行了。那时在曲艺团旁边还有一个棚叫于家棚,棚子都是个人盖的。按传统,还要举办拜师仪式,让我找个保人。当时我找不到保人,师傅就给我找到了两个老团长,也是老艺人,人都特别好,一个是冯崇渭,一个是付永昌。他们对我说,小啊,我们给你当保人了,你可不能学着学着就跑了,走上这条路就得坚持啊。我表态表得山响啊,确实就是喜欢这个。这是在于家棚搞得的拜师仪式,我也给师傅承诺了,我好好学,绝不会半途而废。师傅也给保人表了态,一定尽最大努力教我。这是传统的仪式,我觉得现在也有必要有这种仪式。
拜了师,立即见效。第一个月就给了我六块钱,那时东西便宜啊,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两块来钱就满够了。自己留下两块,给俺娘四块。俺娘心疼我:孩啊,你这么小就让你养家挣钱了。这一年我十二岁。后来有记者采访我,问我最高兴的事是什么,我就说是第一个月拿到六块给俺娘四块钱的时候,孝敬俺娘了,减轻了俺娘的负担。我拜师的第二年,俺师傅就把好多事全都交给我了,包括制作影人,演出,还有准备工作全交到我这里了。这样长了就出来闲话了,包括戏团里的一些老师喊着我的小名跟我说,小安,你看你师傅整天光端着杯子喝水,把活都让你干了,你也别干。经他们这么一说,你说我一点情绪也没有吗,也有点。但有一点制约着我,我胆小,心里有点情绪也不敢说,因为那是老师啊。实际上,到了后来,也就是我当兵回来,师傅给我说起过别人的闲话,说正安,我为什么让你干这么多?这时我就给师傅说,师傅,什么也别说了,我完全明白了,我是俺那些师兄弟中水平最高的,怎么来的?都是师傅您叫我干出来的,师傅,我谢谢您!师傅用心良苦啊,这背后都饱含着师傅的爱心和责任。我有时到大学去,给学生也讲这个,我说你不要看老师很严格甚至很严苛,你不要忘了,这个背后藏着的是爱心!可以这么说,在整个山东的曲艺中,没有我不会的,山东琴书、山东快书、渔鼓、落子、大鼓都能唱,我好学爱学是个前提,但是老师愿不愿意教你,你得动脑子了。为了学这些东西,我就主动拉近和老师的关系,第一尊重老师,在老师面前从来没敢大声说话。有事老师们都愿意叫我,也没什么大事,就是跑跑腿,买盒烟,打瓶酒,干点小活之类。再就是一块出发,条件差,老艺人们都喜欢喝水,我比别人多干个活,晚上捡柴火,早上五点就起来烧水,给每个老师床头上闷上茶,老师们起来就能喝上水,晚上他们睡觉我把被子给他们铺好。这都是小事,但体现的是孝心,老艺人们时刻在观察着每一个徒弟。当我提出来想学点琴书、快书之类的,老师就说,好啊,小啊,别人不教,就教你。后来有师兄弟就说,就你小子鬼心眼子多。我说,这都是咱老师,值得尊敬,但尊敬不能光挂在嘴上,得有实际行动,这个没错吧。只要孝心尽到了,老师一定会另眼看你。我师傅很开明,我跟别人学的时候,他从不反对。他说,你学这个,咱的皮影都能用着了,我不生气。
我与师傅的感情一句两句说不完。再说个事吧,这是到了师傅晚年的时候,师傅身体不行了。2000年的一天,在医院里,师傅把我、俺师娘、师傅的两儿两女叫到病床前,做了两个决定。第一个,把他演皮影的所有用具,包括从师爷传下来的,都给我。当时俺师娘还说,你还有俩儿来,怎么不给他们留点。师傅说一件也不给,师娘问为什么,师傅说给他们都糟蹋了。师傅说这话是有原因的,他的儿女都不愿意学这个,大儿为了逃避学这个还在外边租房子住,躲避这个。俺师傅私下里对我说,咱这行还有什么干头,自己的孩子都不喜欢。加上后来师兄弟八个走了七个,只剩下我一个留下来。当然,我这些师兄弟走是有原因的,当时文革这一段不让演了,他们也都结婚了,有孩子了,没钱吃嘛,得养家糊口,都改了行了。第二个决定,在师傅墓碑上留下我的名,我在墓碑的中间,刻的是“弟子范正安”,左右是师傅的俩儿俩闺女。一直到现在,我感到很自豪啊,被师傅当成传承人了。我说这个是想突出一点:尊师,只有尊师,老师才愿意真心教你。所以我悟出的道理是,做人要孝敬父母,尊敬老师,这是必须要做的,你没有表功的份,只有检讨的份,检讨自己做的够不够。师傅住院期间,我跟老伴和师傅的孩子同样排班照顾。别看穷,可是我买车早,师傅病重的那几年,从北京到上海看病,只要叫我,我马上就开车去,而且所有花费我从来不和他的孩子们说,你愿意拿就拿,不愿意拿全部由我来出。师傅都看到眼里,他明白。当然,我这个饭碗就是师傅给的,我这一辈子就吃这个饭,做这些也是报答,都是应该的啊。咱现在只恨回报的不够。师傅去世十九年了,俺师娘还在,师傅的几个子女都在,我们的关系相当好,前天,我和师娘一家刚给师傅上了坟。和我做的相比,师傅给我的奖赏过高,我看成是师傅对我的鼓励。徒弟能上师傅的碑,这么多年我还没看到过,说这个就是想告诉后人,要讲孝道孝敬,这个光荣传统不能丢。再一个是,单纯从狭隘的个人主义出发,你想收获必须付出,人世间的事是等价交换的。感情也是这样,我希望周围的人、身边的人要明白这个。
采访者:泰山皮影与其他地方的皮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?
范正安:泰山皮影与其他地方的皮影有很大的区别,主要体现在全,一个人要把所有的活全能做了。泰山皮影号称“十不闲”,一个人连演、带唱、带伴奏。别的皮影戏,演员是演员,做皮影的专做皮影。泰山皮影不行,演皮影的要求会做皮影,做皮影不是可会可不会,而是必须会。这方面我与俺师傅也探讨过,与我们人手少有关,慢慢就形成传统了。招来的演员必须先会做皮影,做好这个才能教给你演皮影,这是我们泰山皮影的教学特点。泰山皮影要求自己编剧编戏,自己刻皮影,自己演。除了传承的传统的那部分,不能演别人的,都是自己的创作,这样等于融会贯通了,各个环节没有制约了。这对我是很大的好处:反应迅速。你说个大意、主题,我很快就能编出剧本,在思考一个节目时我已经开始刻皮影了,小的题材,有时紧紧手,当天晚上就能演了。当然,这得分做什么人物,比如古代的穿铠甲的人物,做好可能需要一个月。但现代人物就简单多了,衣裳上都没图案,特别是原来的工农兵,蓝褂子黑裤子,剪下来涂上颜色就行,这个做得最快。
采访者:您是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专心演皮影的?
范正安:这样到了1994年,得到一个消息,我又要来了文件看,说是工龄满30年的,可以提前退。我一看,时候到了,退!为什么退?还是为了皮影的事,这些年也一直没有放下。食品公司属于商业系统,当时每个系统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,阵容挺大,人多,我在里面还是主要成员,每年都有一些活动,搞活动我就演皮影。另外,这些老泰安人、老兄弟们,都知道我挑影子,一看我当兵回来了,有机会就让我演。特别是到了1980年以后,改革开放了,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,老人做寿有的又想起了老传统了。把挑影子的叫来,给老人家演个皮影,这个我参加的不少,过去叫唱堂会。我演还有一个优势,传统的有定式,你在喜宴上必定要有的福禄寿喜,特别是喜神必须要出现,喜神就是月老,月老栓红绳你才能走到一块儿啊。然后,再根据现场人物的情况,看看男女双方是干什么的,我就做成相关皮影,说说青年男女的成绩贡献,这样双方家长、青年男女都高兴。1994年以前,我还干了一段婚礼司仪。我干这个的特点,一是健康,没有低俗的,第二是热闹,别人只是像播音员似的说,我又加上唱,还有皮影,他们没法和我比。别人一场500元,我是800元,有时还得排队呢。到现在我还是咱婚礼协会的副会长呢。人家喜欢我主持的生动欢乐。你比如,我的开场词:“泰山脚下尽朝辉,一对新人要结婚,郎才女貌多般配,小两口今晚一个被窝里睡,哎,那位先生你别急,也没我来也没你,我们只是来贺喜。”你不能严肃得像播音员似的,得稍微有点诙谐,还不能过了。利用这种说唱的形式为大家服务,目的还是牵挂着我的皮影,白天主持婚礼,晚上演一场泰山皮影。婚礼上主要还是演麒麟送子,这是演出最多的。主要内容是老的积善行德,小两口结婚以后麒麟送来孩子,吉祥如意。利用在民间服务的机会,延续传承泰山皮影,既是谋生的手段,也是宣扬传统文化,受老百姓欢迎。都说,老百姓说好那是真好。我这个皮影中间没有夭折,是在连续不断的传承发展中,一个重要原因是能适应外界的形势。外界形势一变你就不适应,那你只有消亡,适者生存嘛。根基是什么,还是在学徒演出的时候受到了老师严格的培训,再加上后天自己的好学,归根结底是你肚子里有东西。所以1971年到1994年一直在干着,1994年退休后就更心无旁骛地干了。
采访者:能说一下泰山皮影申报非遗的事吗?
范正安:到2006年是一个转折点,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,我们国家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词也不是咱们国家起的名,是联合国起的。传承我们的皮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,我一想这是好事,春天来了。这是从国家层面提倡这个事,还要相应制定一些政策进行保护。
说到申报的事,有些细节原来一直没有对外说,今天校长亲自来采访,我得说一下,我的申报过程并不十分顺利。2006年我当时知道消息后,就找到文化局下面的一个科,人家说,老范,你那个不行,人家是从源头上搞,你是源头吗?我说,泰山皮影咱是源头,但就全国皮影来说咱不敢说。人家说,那你就不够资格。后来我一查资料,没有这一项。但我不知人家这么说的目的。这么一来,我没有申报成,不够格啊。尽管我心里有点嘀咕,怎么就不够格呢?但也没胆量去找。这事我还得感谢俺的儿子。到了2007年,俺儿维国搞了个泰山皮影网。上网的第三天,北京来电话了。打电话的人叫魏礼群,是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委会的,管着木偶和皮影这两项。就是这个人,让我的皮影成为首批非遗,我很感谢他。他给我打电话问,我去泰安三次,一个人的皮影怎么就没找到呢?我两天以后到泰安去找你。第三天就带着两个助手到了泰安,就在今天采访的这个地方。他说,把你的老物件都拿出来我看看,他看得很仔细,又让我支上幕布演了演。他问我,我们的申报马上就结束了,你怎么没有申报呢?我不好说别的,就说自己衡量着可能不够格,就没报。他说,你通知你们局里,我下午去找他们。那时候局长还是胡立东,他没出面,是梁孝东去的。谈完后,魏礼群问,泰山皮影这么好,我来了三趟怎么没报呢?后来知道,当时,咱这边回答给他说,有泰山皮影,但老艺人死了,这是实话,我师父2000年去世的。人家问有徒弟吗?回答说没有。这有点不合事实了。也可能是我师父在的时候,我不大出面的原因,人家不大了解有我这个徒弟。魏礼群说,全国一个人的皮影只有泰安有,你们抓紧报,我就负责这个事。局里立即组织人马张罗申报,很快就报上去了。一报就批下来了。我就佩服人家魏礼群这个做事的风格,是真负责任啊,为这一个事来三趟。知道消息后又亲自来做工作,让人感动。
从后来看,也证明了咱泰山皮影的价值。2007年,在北京世纪坛搞了全国非遗保护展,让人们看看,从2005年以来的两年间的成果。展了半个月,当时去了三家皮影,第一个的唐山的大团,第二个是湖北云梦的四个人,一个人的就是我。从安排上也没把咱放到重点位置,可能是咱人少。但世纪坛这次展览,对我个人是个巨大的鼓励,因为国家领导人的给咱高度肯定。当时是展览的倒数两三天,我正演着呢,回头一看,这不是温家宝总理嘛!事先都没告诉。总理离着我就一米多,到了我的后台来了,我不能停,就又演了十来分钟。这时,温总理的秘书说了,老范,停停吧,总理要和你握手了。我马上停下来,总理主动握着我的手,我说,总理您在百忙中来看我们,这是对传统文化和我这个老艺人是最大的支持。温总理说,这是我们应该干的。一谈就谈了大概四十分钟。总理问我,当地政府对皮影是怎么保护的,我说,当地政府制定了五年的保护计划。我以为这么一说搪塞过去就行了,哪知道总理继续问,五年都有些什么措施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,咱哪里能掌握那么多信息?想了想个大概其就说,我们是有个五年的计划,第一步是摸底,掌握谱系传承,有些专家要介入,光我自己肯定不行。第二步是把现有的影人、道具做一个保护计划,别把老家什给丢了。第三步呢,再找当时的专家,就泰山皮影再深入地挖掘一下。第四步是,政府部门准备无偿给我提供一个场地,便于在那里教徒传承。总理问第五步呢?我说第五步是,在全国范围内,找有关皮影方面的专家学者来泰安进行学术交流,让我们泰山皮影学习别人的长处,也看到自己的差距。总理说好,李长春在旁边说,如果全国都这么办,我们的非遗保护就有希望了。我说的这些话是泰安政府要做的事,也是我个人非常期盼的事。从现在看,政府也做到了这一步了。你看我现在在老影剧院的演出场地,这是当时我找了宣传部,宣传部把这个事交给文化局,由文化局落实的免费场所,挺好。虽然中间有点小问题,但一直用着。咱也是想给政府交点租金、交点税费,但领着这么一大帮人负担太重了。人家是带徒弟,由徒弟给老师钱,我是给徒弟钱。我是想把这些人留住,如果生活都保障不了,谁能跟着你这么长时间?现在的年轻人你给工资很低了他干吗。
采访者:泰山皮影这么多年了,您对未来的信心怎么样?
范正安:我认为最坚定的事,最有希望的事,是我摊上了一个好时代。什么好时代?党和国家重视传统文化,有国家和政府支持传统文化,有专家们尽心负责的研究,我是充满了信心。如果不是外部环境这么好,你就是本事再大,要想发挥出本事,在全国造出影响,也不可能。我最担心的是,一开始我也拉了,我是几十年积累了,而且是从来没有停过,后来人要想达到我这个水平,必须倍加努力。但我很欣慰的是,我这些孩子都听话,从小都在学,都不嫌弃这个事。包括我这个小外孙女,从小就受我的影响,这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研究生。她经常传一些传统文化的资料给我。儿子也是全力以赴地做这个事,闺女也是,我把一满家子都拉进来了。我现在是三十多口人干这个,小孙子的基本功掌握的真不孬。他现在上初中了,不能太耽误他的功课。但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都过来练练,给我看看,别把学的忘了。一个是多练练,再一个呢,我每次都给他灌输点新的。我这个外孙女,看似鞭长莫及了,跑到北京去了,但离我北京的剧场近了,只要有空到剧场来,就得参加实践去。
我为什么强调师徒传承?是觉得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的学习环境了,当时我一拜师就带着小被子到俺师傅家里去了,成了师傅家庭的一员。师傅炒菜,我拉风箱,师傅的孩子也是我抱起来的。与师傅朝夕相处,学习技能,学习做人,那种环境现在的学生没有了。我认为,从传统文化、非遗传承来说,一些老的艺人大多是用这种方式传承的,这个非常便利学习,是全方位的学习,也是效果最好的学习,目前没有这种师承环境了。课堂教学是一种方式,但传统的学生跟着师傅,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传授,对许多非遗来说,特别是像我这种十不闲的技艺,是必不可少的。手把手的教往往只有传统师徒传承能做到,课堂上很难做到,做不到就会影响学习效果,影响传承。
我个人很感谢校长你们对泰山文化的重视和研究,这是每个泰安人的事。你们今天采访我的这个地方(蒿里山),这是禅地的地方,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,我查了历史资料,这是周成王定的。如果说还有别的心愿的话,只有一个,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,如果市里打算保护开发,我立马搬迁,让位给更好的发展,这是三重空间的第一重,太重要了,现在这种利用形式太可惜了。
【采访手记】传统艺人的不易从范先生身上可见一斑,学艺就是做人,万事一理,其学徒学艺的历程,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。能走到今天,其兴趣、其艺德、其悟性的作用巨大。作为传承人担心传承事,师承渠道形式的变化,是他的忧虑,徒弟的保障也是一直挂心的事。真希望能有个文化传承的奥运会,那样可能就真重视了。靠着一个人的力量做到现在全赖坚守的力量。范先生最后提到的蒿里山保护与开发,充满了社会责任感,这是不是与老先生经常表演泰山石敢当皮影戏有关——充满了敢当精神。
此文摘自王雷亭编著,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《泰山旅游口述史》之旅游实业篇,内容略有删减。
初审编辑:
责任编辑:路时川